胎牛血清(Fetal bovine serum,FBS)是最广泛使用的细胞培养基生长补剂,因其含有大量的胚胎生长促进因子。胎牛血清一般由配有特殊设备的屠宰场制备。在屠宰时,有时候可以发现怀孕的母牛。这时,有特殊设备的屠宰场就会将胎牛消毒后送往特殊的制取设备中,取得其血液,并通过离心等方法,经加工后就成了FBS。胎牛血清的制备过程中会使胎牛忍受强烈疼痛,因此胎牛血清的制取存在一定的伦理学争议。
最近,两个不同的实验室进行了体外实验,这些实验应用了相同的实验程序,并使用了来自同一供应商的细胞和FBS[1]。令人惊讶的是,两组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细胞反应差异的一个原因是细胞培养基中添加了不同批次的FBS。鉴于整个研究过程中,普遍使用细胞培养,因此确保研究产品的可重复性,以及符合伦理的采购程序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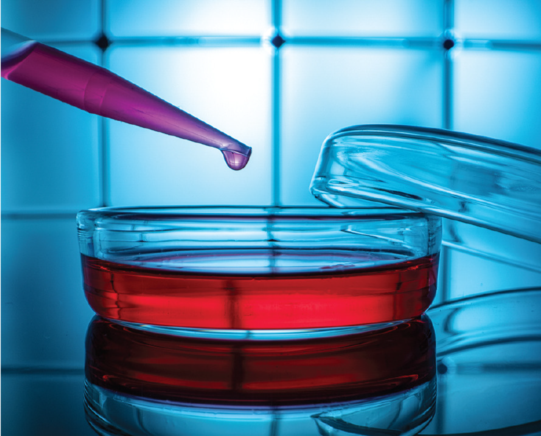
图源 Science
为了让细胞和组织在体外维持和增殖,需要确保具有生长因子和营养物质的最佳环境,这通常是一种液体介质。自首次在青蛙淋巴液中维持青蛙神经纤维的体外细胞培养实验[2]以来,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最佳培养基成分。多年来,已经开发了动物源性培养基和人工培养基。例如,人工培养基包括Eagle培养基、改进的Eagles培养基 (MEM) 、Dulbecco的MEM (DMEM),以及 Ham的F10、F11和F12。然而,并非所有细胞都能在这些人工培养基中生长。1958 年,人们发现细胞可以在含有FBS的培养基中保持更长时间的活跃生长[3]。由于有研究还报道了,几种不同的人体活检和原代细胞培养物可以在这种补充培养基中成功增殖,这导致了今天人们仍在培养基中广泛使用FBS。
FBS是一种取自牛胚胎的血清,含有广泛的营养物质以及过量的生长和粘附因子,并且抗体含量低。FBS价格相对便宜,因此FBS成为几乎所有真核细胞培养基的补充剂首选。大多数细胞类型在增殖和活力方面似乎对FBS反应良好。然而,FBS在细胞培养应用上的第一份报告中,两个重要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FBS 可能含有影响实验质量的毒性因素,并且在不同季节获得的FBS显示出明显的性能差异[3]。
在不同地区,以及一年中的不同时间生产的不同批次FBS,对细胞有不同的影响并不奇怪,因为FBS是一种成分未知的生物制品。通过对细胞形态、生长速率和活力的影响,以及改变实验条件的反应,这种差异可能在细胞培养中变得明显[1]。当必须获得新批次的血清时,为了避免实验室内细胞性能的差异,需要费时费力地进行批次测试,使用实验室中可用的细胞系价差实验室内质量标准。虽然这解决了内部不一致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实验室间的一致性问题,因为不同实验室无法获得同一批次的FBS。当体外方法用于应用研究时,例如人体细胞的临床前研究,或药品和化学品的监管安全测试,实验室间的重现性变得至关重要。由于这些实验室间可重复性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7年开始不鼓励使用FBS,特别是用于化学品的人类健康风险评估[4]。

自1989年以来,牛海绵状脑炎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itis,BSE) 危机推动了替代牛衍生材料,特别是在临床或医药产品中。由于非人类病原体的潜在污染、引发不需要的免疫反应的风险以及产品可重复性的问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5]和欧洲药品管理局[6]不鼓励在用于人类临床应用的细胞和组织培养中使用FBS。
需要用更具生理相关性、使用安全、组成一致的培养基,代替组织培养基的FBS补充。现在有其他替代选择,例如人类或植物提取物,或完全化学成分确定的培养基。对于涉及人体组织和细胞的实验,首选不含FBS的培养基,因为FBS 可能含有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和异种蛋白质,因此可能特别不相容[7]。在将体外方法用于临床应用的情况下,已经引入了无异源介质,例如人血清或人血小板裂解物。然而,这些也是生物制品,因此存在批次间差异[8]。在重现性和安全性尤为重要的领域,人们越来越关注开发和使用化学成分确定的培养基。与FBS不同,化学成分确定的培养基通常是细胞类型特异性的。因此,对于特定的细胞类型,使用或开发了一种不同的培养基。
在FCS-free数据库(网址:https://fcs free.org) 中,可以识别商业来源或科学文献中描述的各种细胞类型的几种现有定义培养基。例如,对于经常用于生产重组治疗产品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广泛描述了开发合适的无FBS培养基[9]。目前,已鉴定出22种不同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无FBS培养基。至少有19种无FBS培养基可用于人类MRC-5和灵长类动物Vero细胞,这些细胞广泛用于疫苗生产。间充质细胞是从人类脂肪细胞中分离出来的,用于人类再生疗法,并且已经为此开发了许多不含FBS的培养基。
不可否认的是,商业来源的合成培养基存在一些缺点。首先,出于商业性和专有性原因,使用者通常不清楚培养基配方。因此就不可能确定特定成分的相对量,从而确定它们对细胞和待测物质的潜在影响。此外,成分还可能会改变。而且商业培养基也很昂贵。在理想情况下,会公布生长培养基的成分,这可能使研究人员有机会专门为其细胞调整培养基。但是针对特定细胞类型,对现有的无FBS 培养基进行调整,可能会导致实验室间的不可重复性。若公布完整配方并进行比较,应该可以确定差异的原因。然而,使用FBS时这不可能做到,使用商业培养基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科研界对用于特定目的的特定细胞类型的最佳培养基能够达成一致。
不含FBS的培养基并非适用于所有细胞类型,因此必须开发其特定培养基,或者理想情况下,可以开发一种通用培养基。目前,不含FBS的培养基初具雏形——由等体积的DMEM和Ham营养混合物F12组成的丰富培养基,辅以重组胰岛素和转铁蛋白以及矿物质硒。其他成分,如生长因子、激素和蛋白质,可以进一步改善培养基[10]。此外,细胞对新培养基的适应[11],以及细胞外基质的底物的选择,已被证明在无FBS时对维持或改善细胞表型很重要[12]。当在一个系统,使用不同的细胞类型时,对化学培养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研究报道将一种化学成分确定的培养基,与每种细胞类型的特定底物相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功能性的人类多器官体外系统,该系统可以维持28天[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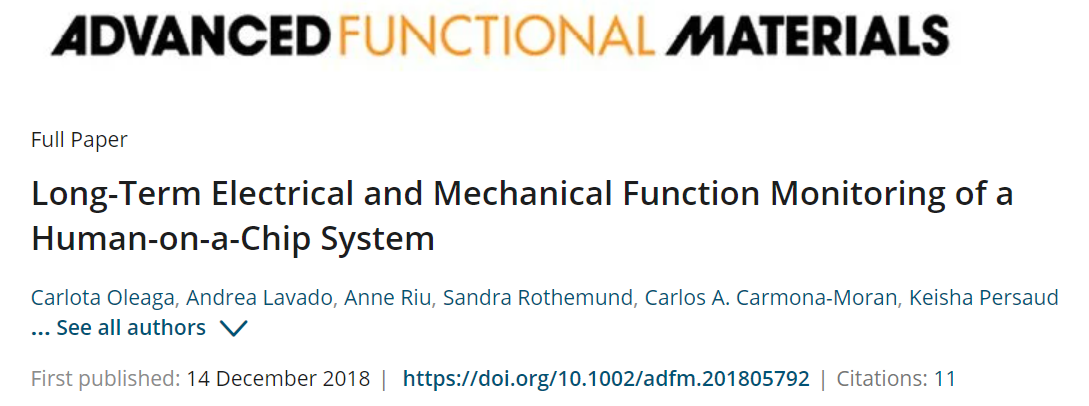
图源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目前,还没有通用的化学成分确定的细胞培养基。现有的某些细胞类型的化学培养基的多样性,以及为其他细胞类型开发培养基的工作,对于取代常规FBS培养基造成了巨大障碍。无FBS下开发新的体外模型,且使用者就特定细胞类型的最佳化学成分培养基达成一致时,将有助于推动无FBS细胞培养的应用。
在何种培养基中细胞和组织表达与生理相关,而何种培养基适合特定研究表型,以及应如何评估新培养基,是科研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目前,人们用作比较参考的结果,仍然是从FBS培养基中生长的细胞获得的。然而,这些结果可能并不总是相关的,并可能引发误导[14,15]。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对于人类细胞和组织系统,应与从人血清中培养的细胞中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但是这种方法与FBS一样,应考虑可能的批次差异。
体外研究,对应于体内研究,是生理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注意每个导致不可重复的潜在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案。其中,细胞培养基中添加FBS是原因之一,而开发无FBS培养基,对于确保一致性的、可重复的结果,以及安全性的产品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H. Barosova et al., Toxicol. In Vitro 75, 105178 (2021).
[2] R. G. Harrison, M. J. Greenman, F. P. Mall, C. M. Jackson, Anat. Rec. 1, 116 (1907).
[3] T. T. Puck, S. J. Cieciura, A. Robinson, J. Exp. Med. 108, 945 (1958).
[4] OECD, “Guidance document on Good In Vitro Method Practices (GIVIMP)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 vitro methods for regulatory use in human safety assessment” (OECD, 2017).
[5]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Guidance for industry: Characterization and qualification of cell substrates and other biological material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viral vaccines for infectious disease indications” (HHS, 2010).
[6] EMA, “Guideline on the use of bovine serum in the manufacture of human biological medicinal products” (EMA, 2013).
[7] N. Bryan, K. D. Andrews, M. J. Loughran, N. P. Rhodes, J. A. Hunt, Biosci. Rep. 31, 199 (2011).
[8] K. Bieback, B. Fernandez-Muñoz, S. Pati, R. Schäfer, Cytotherapy 21, 911 (2019).
[9] K. Landauer, in Animal Cell Biotechnology (Springer, 2014), pp. 89–103.
[10] J. van der Valk et al., Toxicol. In Vitro 24, 1053 (2010).
[11] M. S. Sinacore, D. Drapeau, S. R. Adamson, Mol. Biotechnol. 15, 249 (2000).
[12] M. Cimino, R. M. Gonçalves, C. C. Barrias, M. C. L. Martins, Stem Cells Int. 2017, 6597815 (2017).
[13] C. Oleaga et al., Adv. Funct. Mater. 29, 1805792 (2018).
[14] A. J. Lau, T. K. Chang, Toxicol. Appl. Pharmacol. 277, 221 (2014).
[15] Z. Wei, A. O. Batagov, D. R. F. Carter, A. M. Krichevsky, Sci. Rep. 6, 31175 (2016).













